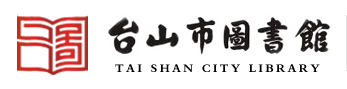1848(道光28)年美国西部的加州发现金矿之後,美国资本家由於投资开发,需要大量劳动力,於是通过人贩子,诱骗中国贫民去当劳工。十多年後,在1862年7月,美国国会通过建筑太乎洋铁路法案,也需要很多的劳工为其建筑铁路。其次,1856年又值邑内“土客”械斗,社会一片混乱,四乡农事不振。加上1860年(咸丰10年)英法联军入京,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,国家陷於半殖民地状态,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,允许外国人在国内招收劳工。这样,我邑的劳动人民便一批又一批地大量离乡土、别亲人,到异国去谋生,逐步形成了侨乡。
一、雏形阶段
民国初期,社会有短暂的稳定,侨滙亦有所增加,邑民的购买力也随着提高,农村生产也恢复了生气。台南濒海地区的广海咸鱼、芥兰,都斛菜花,海宴的的鲜蚝和咸虾,赤溪的酸菜和紫菜,台北丘陵地区的斗洞茨菇,潮境萝卜,冲萎乌豆,坂潭和浮石的番薯等土特产都发展起来。为了适应侨眷建造房子的需要,各乡镇的砖瓦窑也相应地发展。
侨滙收入多了,可以供给子女读书,因而学童也就增多了。民国成立後,台山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,许多私塾改为小学,各区乡利用姓氏的宗祠开办小学,也越来越多。
然而,社会的稳定,却如昙花一现,稍瞬即逝。1926年以前的这段时间,是台山社会治安最乱的年代。侨乡财多招贼祸,政府又无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人们只好独资或筹集资金建碉楼、购枪械以自卫。联安地区12条自然村,便有碉楼30座。1930年,县人编写的《和平实现後建设新台山》一文中说:“碉楼一类,数逾五千。台山经济力之消耗於此不合理之建设者,已在五千万金以上。”这个时期台山只是侨乡的雏形。1913年《新宁杂志》12期载:“在咸同以前,最为闭塞,是鄙俚之县,盖交通不便,人皆闭关以自守也。”“上下新宁之界限,割划如鸿沟,凡所有出产之物,只在产地为销场。而非产地者,则不但无其物,且不识其名,偏枯之弊,殆天地所以介别区域者欤。”
二、形成时期
台山侨乡的形成,还是在新宁铁路建成之後。1937年,全县公路网基本完成,共有31条公路,长达400公里,内外畅通,南北交流。在三十年代前後,台山侨乡每年侨滙收入,常在千万美元之数,成为巨大的购买力。而台山物产不丰,只好仰求外县、外省和国外。粮食、副食品、纺织品、日用百货、建筑材料等,通过新宁铁路运进台山来。这样,以外购内销为特色的台山商业市塲,出现了畸形的繁荣。同时,也把台山卷入了世界市塲。按1938年3月国民政府外滙核算办法,每元国币折合美元3角计算,输入总值为3亿美元,输出总值则为1000万美元。
台山海外华侨多,归国华侨自然也是日逐增多。华侨回来与亲友团聚,固是常情,要办的事情,主要的也是三件,一是婚姻嫁娶,二是建造房子,三是买田置地。乡人口头禅“置田立宅”,即谓此也。1896年(光绪二十二年)新宁知县李平书写的《宁阳存牍》:“宁邑地本瘠苦,风俗素崇俭朴。自同治以来,出洋之人多擭资回华,营造屋宇,焕然一新,服御饮食,专尚华美,婚嫁之事,犹斗靡夸奢,风气大变。”据三十年代调查,白沙的望楼岗、双龙、塘口、李井、牛路的33条自然村,在这个时期就兴建了266座楼房。三合地区20多条华侨新村,其中多数是这个时期建筑的。陈宜禧家乡的美塘新村,全村十多座楼房和斗山浮月村的楼房都是建於这个时期。此外,大江、水步、三八、附城、四九、冲蒌、斗山、端芬、广海、海宴等地,也兴起建新房、立新村的热潮,四乡面貌出现很大变化。
侨滙的递增促进了城镇改造和建设。从1924年开始,台山县城便拆城墙、修马路,增建大批店铺楼宇,与西门市连成一体,人口增至2万多人。接着,斗山、大江、都斛、白沙、公益、端芬、三合、三八、四九、冲蒌、广海等墟镇也相继进行改建,并新建了冈宁、同安、公和、蟹岗、环海等墟镇。统计全县有106个墟镇,最密集为端芬的大同市一带,方圆一公里竟有5个墟市(大同市、汀江墟、那泰市、西廓墟、塘头市)。
市镇的改造和兴建,显示了商业的繁荣。墟镇多有茶楼、饭店、旅馆、苏杭铺、百货店、山货店、金铺、钱庄、乃至烟窟、赌馆、妓院,每个墟镇成了一个中心消费点。据沙坦市的调查,有杂货铺17间、茶楼旅馆10间、药材铺9间、礼饼铺4间、猪肉店10间、糖烟酒店6间、布疋百货店8间、木料缸瓦铺7间、医务所8间、金银铺票号11间、水菓店5间、理发店3间、妓院6间、鸦片烟馆14间。从这个小墟镇行业的结构,便可见当时侨乡社会的一斑。
老一辈华侨出国前,多为文盲、半文盲,在外交往深感不足,甚至与家人书信来往亦诸多不便,故而希望子侄有文化。这样就形成华侨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的传统观念。1933年的地方教育经费为822427元,是五邑之冠。台城有台中、台师,女师三所县立中学;还有私立学校8间,包括商科、会计、汽车与无线电职业学校。在斗山、白沙、端芬、都斛各有中学一间,还有公益的省立越华中学,台城两所英文补校,共是20间。1947年公布的数字,除上述中学外,尚有中心学校112间,保国民学校1010间,私立小学360多间,全县学生将近10万人。
侨乡教育事业的兴衰,与侨滙的增长、减退,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这是侨乡教育的一个特点。正因为它牵涉到千家万户,培育人才又关系到百年大计,所以侨乡的杂志、族刊都有“教育专栏”,及时报道学校消息。1934年在《新宁杂志》有一篇文章,题为《学生与学死》,兹节录之:“所谓学生者,即学习人类生存之道也”。“亦以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为教育之三大纲领者,即此义也”。“出则为国家有用人才,处则为乡邦民众之指导,必如是而学生之意义始见,亦必如是而学生之责任乃尽也”。并批评:“近数年来,台城中级学生,竟有置功课於不顾,而偷住旅馆,叫娟妓,赌麻雀,设烟局的邪气歪风”。并曰:“以此求学,名为学生,实则学死”。以此说明邑人对教育之关注。
侨乡的形成,不论农村的变化,城镇的建设,还是商业的繁荣,文化教育的发展,都出现新的局面。
三、社会对侨眷的影响
侨乡的台山,与危难深重的祖国一样,饱经辛酸。官吏贪污鄙劣,置人民痛苦不顾,与乡村的豪绅狼狈为奸,鱼肉乡民。四十年代的《康和月刊》登载题为《为什麽要打倒土豪劣绅》的文章,罗列了豪绅“重利敲剥、诱奸妇女、侵吞公款、摧残教育、欺凌弱小”的五大罪恶,便是对当时贪官污吏的控诉。
侨乡的台山,虽然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,但仍深受封建势力的束缚。豪绅们利用封建意识、宗族观念,划地为牢来统治侨乡人民,以嫖、赌、饮、吹来腐蚀侨眷青年,从中渔利。此外,社会治安不宁,也给侨眷极大的威胁。1925年冬,广海夹水村刘孔就、谭添宗、谭添活从外洋回来建新房和结婚,陈祝三匪帮认为“金山伯返乡,荷包肿涨”,便派出黄华带领一伙匪徒去攻打夹水村,幸发现及时,且有增援,遂毙其一匪,然尚被掳去村民三人。从1916年至1926年,台山社会是盗贼世界。广海地区被贼匪焚烧村庄24条、房屋1114间、碉楼25座;受劫村数57条,受劫户数2501户,被掳人数646人,杀害人数38人。其中侨户、侨眷是主要的受害者。
华侨在外含辛茹苦积蓄一点钱回来,要建房子,也免不了受豪绅诸多为难。比如“打灰坎”、“搭木厂”,少不得要借用公地。豪绅就指使村中散仔要主家请宵夜(吃夜餐),否则,便抛杂物下灰坎或偷盗木材砖瓦,无风起浪,使你不得安宁。华侨想不到在外巳受尽欺凌,回到家乡亦成为刀下之俎。总之,在贪宫污吏、地主豪绅的统治下,侨乡台山是不宁静的。
侨乡台山的妇女受“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”的四大绳索束缚,还受着“贞节”的传统观念的约束。自亲人离家出洋,她们便挑起家庭重担,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,耕作农田,饲养家畜,操劳家务,谨守闺帏,抚儿育女,过着“守生寡”的生活。广海夹水村11人去古巴,只有两人临老回来与家人团聚,其他连最後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有一首台山歌谣描写侨妇苦闷的心理:“青春守生寡,千里迢迢谁共话?想来想去心如麻!细想他,虽在天边云脚下,三更还望他回家!”
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,离奇怪事也层出不穷。一些老妇人不待儿子回来就娶媳妇,用“生鸡上头”(以雄鷄代表新郎)。谁都知道,鸡怎能代表人?可是在民国二十年前後,六村南乔村就发现一幕戏剧性的婚礼。新郎刘××旅居美国,其婶娘陈氏觉得他是一根独苗,应及早成婚,於是在家与他在冲萎定下一位李姓女子为妻,然而,“金山郎”久等不归,陈氏婶娘急不及待,在家里用“生鷄”权当新郎成婚。虽然後来团聚,但亦虚度不少年华。光绪十九年的《新宁县志》和《赤溪县志》的烈女传,其中有不少是侨眷。赤溪连兴村的蓝伙招,五岁便许给正金村朱伙茂。当她15岁时,未婚夫往秘鲁谋生,年复一年,游子归期杏杏。蓝伙招27岁那年,朱的父亲去世了,按旧礼教她要回男家守孝。後来,她50岁才知朱伙茂客死异国。直至1963年,她也63岁了,才知封建礼教害了不少人,但可惜太迟了。
1929年,北京台山青年学会出版的《台潮》第八、九期刊载的《女权发达须以教育为条件》中,有题为《不幸做了台山的一个女子》文章,内有“台山算是中国压迫女权头等的一县了。之说。在男尊女卑的观念支配下,尽管台山教育相当发达,但女子教育犹未普及。据《台山至孝笃亲月刊》1949年第13期刊载的《台山教育动向》报导:1949年台山中等学校男女学生比例悬殊很大,初中女生占四分之一,高中女生仅占七分之一。